
艾雯的「黑灰白花旗袍」。(藏品/艾雯捐贈,圖/國立臺灣文學館)
【我們為什麼挑選這個藏品】
許多作家喜歡說創作來自於生活,但生活其實也可能限制創作。經濟因素、家庭因素、健康因素,不能寫的理由太多了,如同堅持書寫的理由一般,族繁不及備載。
「女人從事寫作的結果:世上少了一個好的主婦,而多了一本壞書。」如果身為一名女性創作者,體弱多病,同時又是一位母親,當看到類似的評論,應該壓抑自己、放棄寫作,去符合某種社會期待的賢妻良母形象?或者不顧一切成就自己?
但誰說只能二選一?艾雯表示:我全都要!要做好主婦,也要寫好書;要在紙上發展才華,也要在布料上彩繪自己與家人的美麗家居。女作家艾雯善用針與筆,以服裝設計、手作、收藏,盡情發揮巧思,經營有滋有味的生活,接下評論者的戰帖。
面對生活各種難,怎麼超越限制、堅持美和創作?且讓我們從艾雯旗袍的故事說起,嘗試尋找實踐的靈光與祕訣。

艾雯的「黑灰白花旗袍」。(藏品/艾雯捐贈,圖/國立臺灣文學館)
「我喜歡拈針引線,僅次於執筆寫作:可以一任心意構想、設計、剪裁。從老到小,為家人一針針納入我的愛心和關懷,一縷縷串起我的喜悅和祝福;為自己添製一份美好和振奮;為住屋增加點色彩和溫馨。在製作的同時,也滿足了另一種創作慾和成就感。」[1]
不撞衫的人生:縫製自己的全能戰袍
那是一件手縫的短袖旗袍,黑、白、灰三色花草植物紋飾交錯,在時間的著色下,彷彿有點水墨淡綠渲染,像是製作者不經意就把某個炎夏午後,庭院裡一方蓊鬱的歲月靜好,在一針一線之間,珍藏於身上,也縫進了心裡。
旗袍的主人是艾雯,「旗袍一族」的一員。
什麼是「旗袍一族」?「旗袍一族」指的是1950年代臺灣文壇一群又編又寫又持家,在紙筆與家務之間撐起文壇半邊天的女作家,包括林海音、潘人木、張秀亞、艾雯、羅蘭、鍾梅音、邱七七等女性寫作者們。

艾雯的「台灣省婦女寫作協會會員證」。(藏品/艾雯捐贈,圖/國立臺灣文學館)
無論文友聚會、工作或家居 ,旗袍都是她們常見的穿著,也是展現巧思、實踐美麗的舞台。不同於日後《花樣年華》、《色戒》等電影所呈現的性感豔麗形象,50年代女作家的旗袍往往並非開高衩、曲線畢露,由女作家們聚會照片可見,她們的旗袍往往是過膝、略微寬鬆舒適,標誌一種端莊優雅的氣質,而受官方鼓勵、應允。許多女作家的女兒想起她們的母親,都自然聯想到旗袍所賦予的典雅,以及母親透過衣飾裝扮流露對美的見解與巧思。
相對於今日成衣普遍,可以用相對實惠價格添購衣物,卻不免在追隨流行過程中遭遇撞衫的尷尬, 50年代女作家或親自手縫,或出設計點子請師傅製作,在旗袍款式設計的限制中,硬是玩出自己的花樣。
林海音懂得在看似素雅的衣料上,繡上一排鮮豔的牡丹;羅蘭能用地攤買的外衫突顯晚宴旗袍的高雅;張秀亞心愛的旗袍靠頸處被蟲咬破了,自己剪一塊山茶花圖樣縫補,就成為獨一無二的設計款。潘人木的女兒回憶母親穿著旗袍在廚房優雅做料理的過往,讓她覺得廚房不是油煙之地,反而有如客廳般舒適,可知旗袍如何撐起時代女性的自信,且不僅外出社交可穿,寫作可穿,忙家務也可穿,彷彿那個時代女作家進可攻、退可守的全能戰袍。
在這一群風格殊異的旗袍好朋友中,艾雯毫不遜色。對艾雯的女兒朱恬恬來說,母親穿著旗袍端莊優雅的風姿,是她深植腦海的美好形象。無巧不巧的是,不管是黑緞織金色鈴蘭花圖飾旗袍、寶藍色織同色古典竹葉圖案絲綢旗袍,或者小葉描邊交錯的白綢印花旗袍,許多艾雯喜愛的旗袍都以素雅的花草植物為飾。或許是彼時流行的布料使然,但這些不張揚卻有細節的生活安排,卻讓人不禁想像熱愛植栽的艾雯,穿上這些旗袍,走進她所喜愛的花草之間,彷彿花仙子般優雅的身影。
她是作家,更是熱愛DIY的生活美學家
儘管50年代就以散文集《青春篇》廣受讀者歡迎,論者張瑞芬也稱讚她是美文的開創者,最早成熟的作家。但艾雯對美的追求從來不限於筆端,她曾在〈針黹之美〉一文中自承,喜愛拈針引線,僅次於執筆寫作,因為當她在針線穿梭間落實自己的想像,不僅實現了對家人的愛心與關懷,也滿足另一種創作慾和成就感。艾雯的創作顯然不只寫在書上,也寫在每個家居與日常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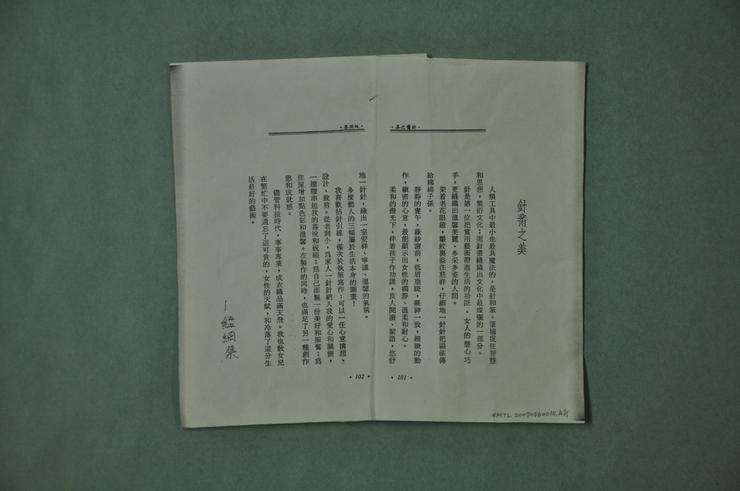
(藏品/艾雯捐贈,圖/國立臺灣文學館)
她是作家,更是服裝設計師、植栽高手、生活美學家,「斜槓」概念發明前的「斜槓」實踐者。
兒時在蘇州和父親一起臨帖、讀書、踏青,看外婆製作玫瑰花雕等「小樂惠」,蘇州那些日子,激發艾雯美的本能,也培養出一個懂得生活情趣的心靈。然而,艾雯不僅是個接受者或實踐者,當她在生活不寬裕的年代,利用現有簡單的材料,製作美化家居的飾品;從選布、配色、設計到剪裁縫製,都不假他人之手,為自己也為家人製作美麗的衣裳,不知不覺間為女兒留下極強的美感暗示,啟發女兒服裝設計的天才。服裝製作因此不只是艾雯個人的愛好,也成為母女共享的美好日常。
低調的華麗:限制中湧動的生命力
艾雯的多才多藝,或許會讓人懷疑她是否有過人的精力?但事實上她從小體弱多病,寫作生涯也不時因為身體狀況而必須放慢腳步,也因為嬌弱善感又是蘇州人,讓文友劉枋聯想到《紅樓夢》中的林黛玉。

艾雯的「暗棗紅背心」。(藏品/艾雯捐贈,圖/國立臺灣文學館)
即使如此,在旗袍妝點的溫婉典雅之外,艾雯對理想卻十分執著,對生命彷彿潛藏火山般的熱情。這種生命情調就好像一套她親自設計縫製的暗棗紅旗袍,沉穩端莊的暗棗紅色搭配修飾身形的同色背心,突顯成熟風韻的同時,卻似乎有些中規中矩,不容易一眼探知內在的底蘊與個性 。但如果靠近再靠近仔細觀看,會發現這件旗袍使用的布料,由黑線和粉紅線交織而成,光線所及之處,閃爍若隱若現的粉色光芒,有種低調的華麗,暗暗湧動的繽紛生命力。
如果生命不可避免是暗面與亮面交錯,不總是能隨心所欲,艾雯在生命的限制中持久地堅持與美相伴。身為作家,早慧且成名很早,但更可喜的是在時間的試煉中堅持下來,直到80歲仍出版《花韻》,描繪她所鍾愛的草木。寫作不輟,完全不是說說而已,寫作或許因身體狀況而趨緩,但卻從未真的停止。

艾雯的「暗棗紅背心」。(藏品/艾雯捐贈,圖/國立臺灣文學館)
生活情趣的經營亦然,移居天母之後,不似以往在岡山、中央新村的家,有庭院可以讓她充分灌注對花草自然的喜愛。但她仍在家中可利用的空間栽花,在陽台上準備了洗澡盆,欣喜期待小鳥、松鼠等小客人的造訪。因健康欠佳而深居簡出,但圖書畫冊、各種文集、上萬套的火柴盒等藏品,滿足生命熱情的種種事物仍圍繞著她。

艾雯的「火柴盒」。(藏品/艾雯捐贈,圖/國立臺灣文學館)
火柴盒中等待燃燒的美
艾雯的收藏,除了旗袍,最引人注目的,就是小巧玲瓏而多達萬件的火柴盒了。這些火柴盒跟她的生活有什麼關聯呢?她抽菸嗎?在觥籌交錯的社交場合、還是在旅遊住宿的飯店與這些火柴盒偶遇?或是有人送給她的呢?無論是哪一種,若非抱著熱情很有意識的蒐集,不可能匯聚這麼多的數量,一輩子也用不完。但其實她的火柴盒也不是要拿來使用,除了蒐集,她還親手尋找圖片、黏貼製作。這彷彿是在告訴我們,生活不僅追求實用,還要有追求美的餘裕啊。

艾雯的「火柴盒」。(藏品/艾雯捐贈,圖/國立臺灣文學館)
雖然火柴盒的來源不見得能夠一一確認,但它們的存在太具生活感,不免讓我們以為那正悄悄透露著艾雯生活的秘密。打開收藏於臺文館中、各菜系餐廳宣傳火柴盒,我們可以猜想艾雯是否曾穿著某件喜愛的旗袍,穿梭其中?猜想她偏愛川菜、西餐還是港點?同時感覺這些火柴盒中遺留許多尚未使用的火柴,像是一種邀請,召喚 同樣對生命有愛、對美期許的人們,接下艾雯的棒子繼續點燃,花火燦爛的熱情。
[1]艾雯,〈針黹之美〉,《綴網集》。
★作家小傳
艾雯(1923-2009),本名熊崑珍,出生於中國江蘇吳縣,14歲之前在蘇州生活成長。1937年全家隨父親至江西大庾任職,不久中日大戰爆發,蘇州淪陷。1940年因父親驟逝,艾雯為負擔家計輟學,但也因為任職圖書館、博覽群書,開啟寫作契機。1944年避難江西上猶,期間進《凱報》擔任大地副刊主編。1949年2月隨家人來臺,最初暫居屏東,1953年8月遷居岡山,開始她生命中「鳳凰花的歲月」,就這樣一住20年,直到1973年遷居臺北。
雖然14歲即離開故鄉,但早年在蘇州所見所聞所感,深深影響她看世界的方式與寫作主題。18歲以短篇小說〈意外〉獲《江西婦女》徵文第一名,自此步入文壇。創作文類包括散文、小說、兒童文學,早期散文與小說並重,60年代中期後逐漸專注散文寫作。她的第一本散文集《青春篇》,被譽為「自由中國第一本散文集」。多年來寫作不輟,創作力豐沛,直到晚年仍持續發表作品。
★延伸閱讀
★參考資料
-
王鈺婷編選,《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31:艾雯》,臺南:臺灣文學館,2013。
-
應鳳凰,《文學風華—戰後初期13著名女作家》,臺北:秀威資訊,2007。
-
林靜端企劃;馬于文、陳昱伶撰文,《打開民國小姐的衣櫃:旗袍、女人、優雅學》,臺北:奇異果文創,2019。
-
「旗袍一族:風姿綽約的世代女作家」特輯,《文訊》10月號(第384期),2017,頁44-69。
★觀測員簡介
劉承欣 政治大學臺灣文學所碩士,臺師大臺灣語文學系博士班。邊走邊看邊寫,總是在摸索學習,如何好好過生活。











